浙江、福建的那些廊桥,竟然有这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框哥说:“对廊桥爱好者来说,蜿蜒的廊屋、繁复的装饰令人赞叹。但就桥梁史意义而言,浙闽木拱桥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桥板之下、不为普通大众了解的桥拱结构与蕴含其中的营造技术。”
框哥说:“对廊桥爱好者来说,蜿蜒的廊屋、繁复的装饰令人赞叹。但就桥梁史意义而言,浙闽木拱桥最核心的价值在于桥板之下、不为普通大众了解的桥拱结构与蕴含其中的营造技术。”
撰文:刘妍
摄影:陈新宇

庆元县举水乡月山村如龙桥建于明代,已矗立了近400年,桥廊与楼、亭结合,造型独特,姿态万千,兼具历史、美学、技艺三重价值,是浙闽木拱桥中首座入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廊桥。
民国五年(1916),一队来自福建的造桥匠人,在浙江省南部章坑村村外北溪上游20余米的高崖之上,完全不依靠电力工具,营建起一座净跨度达30米的木拱桥。次年正月完工,取名 “接龙桥”, 成为日后近百年间景宁通往文成的交通要道。接龙桥廊屋的当心间梁枋底面题写着:木匠宁德县十九都下荐秀坑,绳墨张学昶,副墨张学兰、张学厂……这一支按旧时称呼为“下荐师傅”的秀坑张氏造桥家族是闽东闻名遐迩的木拱桥建造世家,直到今天还有不止一位有过实际造桥经验的师傅在世。
2013年冬,我和另一队福建来的造桥匠人在距章坑村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处的景南乡东塘村,经过五六位大木作匠人近三个月的努力,建起一座跨度16米的小小风水桥。这一支造桥队伍的主墨师傅郑多雄则来自福建省寿宁县坑底乡小东村,是浙江省级木拱桥营造技艺的传承人,早年这一带赫赫有名的“小东师傅”郑惠福就是郑师傅的父亲。这一支造桥家族今天被学界称作“寿宁徐-郑氏”。
这两个家族是近两百年间浙闽木拱桥最重要的造桥世家,资料显示,至今已有七八代造桥传承。据研究,两省现存的百余座木拱古桥中,五分之一出自这两个家族,遍迹于周边廊桥乡县。

横跨景宁县大赤坑村口溪水之上的大赤坑桥为浙南闽北一带多见的桥梁形式。这种编木拱桥不仅为中国传统木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者,也是世界桥梁史上的特例。
手艺行业素来不是小清新的事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并非全然夸大其辞。章坑村的老人告诉我,接龙桥的造桥师傅中就有“徒弟把师父做死了”的事情发生。当桥的主体结构造好,在钉椽子时,“师父穿钉鞋,徒弟穿木屐。徒弟用斧砍师父,师父一跳,掉到崖下……”
这样一种师徒竞争出现于造屋木匠之间并不奇怪——对于强调个人手艺积累的普通匠师同行遍地,竞争自然激烈和残酷。但对于拥有特殊行业秘密的浙闽木拱桥匠人,则未必如此。由于木拱桥技艺的特殊性,造桥匠人会格外小心地将技术秘密守护在家族内部,造桥队伍亦往往以家族为主。我在东塘跟随郑、吴师傅造桥学艺,师傅在向我讲授关键算法步骤时,还会专门到房间里讲,避开其他助手。

木拱廊桥结构示意图。浙闽木拱桥的技术难度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其独特的“编织拱”结构,需要巧妙的设计与准确的计算;二是浙闽山区高山深涧的地理环境对施工技巧的要求。
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浙闽木拱桥”这个术语远没有“廊桥”来得熟悉。对于廊桥爱好者来说,繁复秀美的桥廊通常是当地百姓评价一座廊桥的首要因素。这种只重外表的观感体验,是因为这一类桥梁全部建有廊屋,既保护了下面的木质主体结构,又可作为村子的公共空间,或是用作行人歇脚躲蔽风雨的路亭。
景宁县东坑镇章坑村内的怀胜桥建于清代光绪年间,古朴实用。桥头对面则是建于1960年代末的大会堂。对村民来说,廊桥与礼堂都是他们休息、聚会、赶集甚至举办庆典的公共空间。
但就桥梁史的意义而言,浙闽木拱桥最为核心的价值在于桥面板之下、不为普通游客所了解的桥拱结构与蕴含其中的营造技术。正因如此,早在浙闽木拱桥列入我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之前,“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已经列入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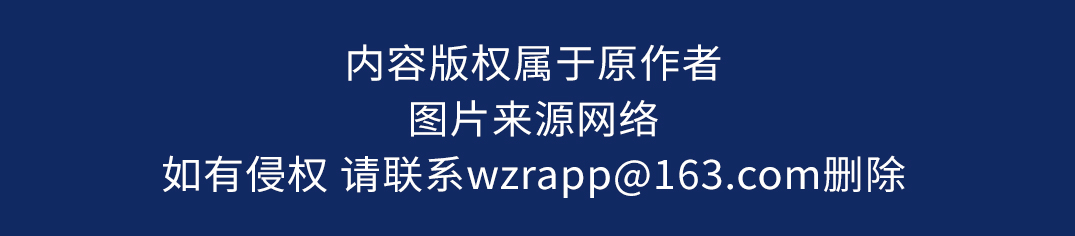
来源:国家地理中文网
编辑:Don
责编:唐台 叶青
审核:金安静
监制:王振辉 翁逻沿
总监制:邓雄杰
最新评论